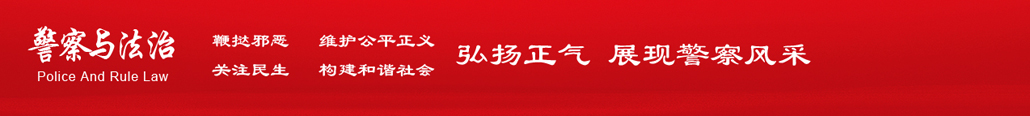新形势下典型劳动关系与非典型劳动关系的认定
曾跃 邓楚伊
数字经济时代,平台经济的崛起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以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重塑了传统劳动力市场的组织形态。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调查,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这些劳动者在管理模式、劳动报酬、休息时间等方面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较之传统视角下劳动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导致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更为复杂。
与此同时,有部分企业亦试图将传统劳动关系中的劳动者形式上包装为承揽关系的承揽人、个体工商户,或者通过多方外包的形式,将劳动者的实际用工主体、合同签订主体、报酬支付主体分散到多个企业,以规避其作为用人单位应承担的义务与责任。此类操作不但加大了司法实务中识别与界定“隐蔽性劳动关系”的难度,也不利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
在此背景下,笔者认为有必要厘清新形势下典型劳动关系与非典型劳动关系的认定边界,这既是破解平台经济治理难题、规范平台经济秩序的关键切口,更是实现从“工业社会”向“数字社会”范式转型的必然要求。
一、典型劳动关系下的认定规则
在因劳动关系确认引发的争议案件中,大多依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进行认定。其中,劳动关系认定的核心在于确认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建立的法律关系是否具有从属性特征,具体包括人格从属性、组织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
人格从属性体现为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作过程的具体控制权,包括用人单位有权单方制定适用于劳动者的规章制度,有权自主决定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与工作地点,有权决定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方式并对劳动者提供劳动的过程进行管理和监督,采取一定的奖惩措施;劳动者必须服从用人单位的指令,不得将其工作交由他人替代履行。
组织从属性体现为劳动者属于用人单位组织体系的组成部分,使用用人单位提供的生产资料、技术条件及管理架构完成劳动任务,其劳动成果亦属于用人单位的业务组成部分。
经济从属性则体现为劳动者对用人单位的经济依赖关系,即劳动者以劳动报酬作为主要生活来源。
综合来看,三者形成递进式关系共同构成了劳动关系的本质。虽然现行法律规定并没有对上述从属性特征进行明确界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则普遍应用前述规则对典型劳动关系进行界定。
二、非典型劳动关系的认定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带来的劳动关系认定困境在于,一方面,劳动者通过平台技术赋能获得了典型劳动关系模式难以企及的自主性,可以自主决定工作时间(例如,网约车司机可以自主决定接单的时间段)、工作地点(如外卖骑手跨区域流动)、劳动供给对象(如网络主播转换合作平台)甚至劳动工具配置(如快递员自备电动车),呈现出“去组织化”的特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趋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其身份处于与平台平等地位的“承揽人”。另一方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并没有完全脱离平台企业的管理,对于平台企业的算法控制而言,其依然处于相对弱势的法律地位。进一步而言,即平台企业通过算法权力构建了隐性的控制机制。例如,平台通过数据分析画像优先分配订单、用户评价直接关系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奖惩规则。同时,平台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手段对其劳动过程全周期监控,实质上将劳动者嵌入平台生产体系的闭环中,形成“弱组织从属性+强经济从属性”的新型支配关系。这种“表面松散自治”与“深层算法驯化”的形式,使该类劳动者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难以适用传统的从属性理论框架而陷入困境。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于2021年7月16日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首次明确提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相关要求,该类劳动者也是第一次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身份进入大众视野。
三、支配性劳动管理认定劳动关系
202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发布首批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专题指导性案例,进一步明晰了典型劳动关系的认定规则,其中,创造性地提出“支配性劳动管理”的概念,并以此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核心。
1. 新就业形态中从属性的理解 首先,对比典型劳动关系认定规则对从属性理论“全有或全无”的判断模式,“支配性劳动管理”创造性地将从属性的强弱幅度作为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在典型劳动关系的视角下,“从属性”是确认劳动关系存在的核心要素,一旦认可双方的法律关系具有“从属性”特征,司法机关基本可以据此认定双方存续劳动关系。而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涉及的非典型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上,一方面,最高法本次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依然没有脱离原有的劳动关系界定标准,并未因非典型劳动关系创设出认定劳动关系的特殊情形。另一方面,考虑到即便是在平等主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平台作为接收服务的一方,同样有权对提供服务方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对合同的履行进行运营管理,最高法并没有完全否定平台在履约过程中的管理权限,而是以从属性的强弱幅度作为认定劳动关系的标准。这既延续了从属性理论中人格、组织与经济从属性的基本框架,又动态回应了数字时代用工关系的复杂性。
2. “支配性劳动管理”判断标准 对于“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判断标准,其核心在于一方对另一方进行了劳动管理,且该劳动关系达到支配性程度。结合最高法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具体内容而言,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判断是否属于“支配性劳动管理”:
1. 劳动者是否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享有自主选择权。以最高法发布的第237号指导性案例为例,该案中的劳动者作为平台企业的配送员,按照平台企业的排班表提供配送服务,出勤时间相对固定,根据系统派单完成配送任务,没有配送任务时便在站内做些杂活。最高法发布的第238号指导性案例中,劳动者作为平台骑手按照排班接单,且不得拒绝平台派发订单。而在最高法发布的第240号指导性案例中,劳动者作为代驾司机有权自行决定是否接单,且平台企业不对其进行考勤管理。对比前述案例可见,第237号指导性案例、第238号指导性案例的劳动者提供劳动时间具有固定性特征、工作任务具有不可抗拒性且仅能在平台企业安排的工作地点完成工作任务,劳动者个人自主选择权非常有限,可见,平台企业对这些劳动者进行的管理已经达到支配性程度。对比而言,第240号指导性案例的劳动者明显对其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具有自行决定和支配的权利,该案的劳动者与平台企业处于相对平等的法律地位,平台企业对其进行的劳动管理并未达到支配性程度。
2. 劳动者是否需要遵守平台算法、工作规则或奖惩办法,且是否具有目的正常性和手段必要性。在典型劳动关系认定的视角下,企业要求劳动者遵守平台算法、工作规则和奖惩办法往往意味着企业对劳动者提供劳动的过程进行用工管理。但在非典型劳动关系的视角下,由于平台需要一定的规则、算法维系日常基本的运营秩序,故对于平台要求遵守的工作规则或奖惩办法,不能一概而论地界定为支配性劳动管理的体现。
以第240号指导性案例为例,该案中的劳动者作为代驾平台的代驾司机,需要接受软件使用培训、进行路考、接受抽查仪容。而且平台根据其成单量、有责取消率等数据,以及接单状况异常情况实行封禁账号等措施,经审理,人民法院最终认定前述管理手段仅是维护平台运营、提供优质服务所需的必要运营管理,而非对劳动者进行的支配性劳动管理。因此,如何划分必要运营管理与支配性劳动管理的分界线,也是个案争议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目的正当性”和“手段必要性”区分运营管理和支配性劳动管理之间的分界线。对于目的正当性,如平台规则是以维护交易安全、保障服务质量等运营目的,该规则可以解释为基于平台正常运营而制定。对于手段必要性,则需要考虑平台规则对劳动者的管理是否为实现正当目的的最小化手段。
3. 劳动者对其报酬、收益分配是否享有协商权或议价权利。获得报酬是劳动者的核心权利,而劳动者对其劳动报酬的协商权或议价权实际体现的是其与平台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即两者是属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或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笔者认为,报酬协商权并非单纯的价格磋商自由,具体包括劳动者是否享有定价参与权、调整异议权和信息对称的权利。以第239号指导性案例为例,劳动者作为平台主播,与平台根据收益情况确定报酬,且在经纪合同的履约过程中,双方曾签订补充合同变更分配比例,由此可见,该案劳动者享有一定的定价参与权、调整异议权,且对收益分配有较高的知情权,与平台企业处于相对平等的法律地位。
- 2021-12-22
- 2020-01-30
- 2021-06-26
- 2020-02-25
- 2020-03-22
- 2020-01-02
- 2021-07-28
- 2020-04-07
- 2019-12-29
- 2021-09-30